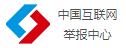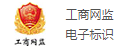纳谏与止谤
——重读《邹忌讽齐王纳谏》有感
臧克家
读好文章,如饮醇酒,其味无穷,久而弥笃。《邹忌讽齐王纳谏》,读初小时就成诵了,觉得它故事性强,有情趣,引人入胜。六十年后,再读一遍,如故人重逢,格外亲切。
古人说:”人非圣贤,孰能无过?”即使君子,也难免有过,不同的是”过也,人皆见之,及其更也,人皆仰之”而已。古代帝王置谏官,自己有了错误,臣下可以进谏。帝王,自以为是”天之子”,富有四海,臣服万民,行为万世师,言作万世法,坐在高高的宝座上,俯视一切。能倾听逆耳之言,采纳美芹之献的,历史上并不多见。但也不能一概而论。也有少数聪明一点的,为了坐稳江山,笼络人心,也能从谏如流。有圣君,有贤臣,使政治稳定,国泰民安,历史上称为太平盛世。像唐太宗与魏征,就是一例。而最突出、最典型的,要数邹忌与齐威王了。
讽谏帝王,是冒险的事。批”龙鳞”(即批评皇帝),逆”圣听”,需要大勇与大智。多少忠臣义士,赤心耿耿,尽忠进谏,结果呢,有的被挖心,有的被放逐。比干、屈原悲惨的故事,千古流传。
因此,对这位勇于纳谏的齐王,既佩服他的大智,也赞赏他的风度。这篇《邹忌讽齐王纳谏》的文章,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宽大明智、精神高尚的形象,事隔几千年,栩栩如在眼前。想当年,他听了邹忌的讽谏之后,立即下令群臣,遍及全国,面刺错误,指陈弊病,不仅言者无罪,反而重赏,这是何等气度,何等磊落胸怀!千载而下,犹令人感奋不已!
事因难能,所以可贵。在同一本《古文释义》里,小时候也读过《召公谏厉王止谤》这篇古文,至今还能背出其中的名句。拿这位厉王和齐威王一比,真可谓天渊之别了。齐威王下令求谏,周厉王却以”能止谤”自喜,天下之人,满腹不平,他要钳住万民的口,自己也捂紧耳朵。”防民之口,甚于防川”,”止谤”使得老百姓”道路以目”。三年之后,土壅(yōng)而川决,这个特大暴君——人民之敌,被”流于彘(zhì)”。
齐王与厉王,那种对待谏谤的态度,得到的结果也截然相反。
历史是一面镜子。《邹忌讽齐王纳谏》《召公谏厉王止谤》这两篇古文,我们对照着读,大有可以借鉴之处。
触龙说赵太后
赵太后新用事,秦急攻之。赵氏求救于齐。齐曰:“必以长安君为质,兵乃出。”太后不肯,大臣强谏。太后明谓左右:“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,老妇必唾其面!”
左师触龙愿见太后。太后盛气而揖之。入而徐趋,至而自谢,曰:“老臣病足,曾不能疾走,不得见久矣。窃自恕,而恐太后玉体之有所郄也,故愿望见太后。”太后曰:“老妇恃辇而行。”曰:“日食饮得无衰乎?”曰:“恃粥耳。”曰:“老臣今者殊不欲食,乃自强步,日三四里,少益耆食,和于身也。”太后曰:“老妇不能。”太后之色少解。
左师公曰:“老臣贱息舒祺,最少,不肖;而臣衰,窃爱怜之。愿令得补黑衣之数,以卫王宫。没死以闻!”太后曰:“敬诺。年几何矣?”对曰:“十五岁矣。虽少,愿及未填沟壑而托之。”太后曰:“丈夫亦爱怜其少子乎?”对曰:“甚于妇人。”太后笑曰:“妇人异甚。”对曰:“老臣窃以为媪之爱燕后,贤于长安君。”曰:“君过矣,不若长安君之甚。”左师公曰:“父母之爱子,则为之计深远。媪之送燕后也,持其踵,为之泣,念悲其远也,亦哀之矣。已行,非弗思也。祭祀必祝之,祝曰:‘必勿使反!’岂非计久长,有子孙相继为王也哉?”太后曰:“然。”
左师公曰:“今三世以前,至于赵之为赵,赵主之子孙侯者,其继有在者乎?”曰:“无有。”曰:“微独赵,诸侯有在者乎?”曰:“老妇不闻也。”“此其近者祸及身,远者及其子孙。岂人主之子孙则必不善哉?位尊而无功,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。今媪尊长安君之位,而封之以膏腴之地,多予之重器,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国,一旦山陵崩,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?老臣以媪为长安君计短也,故以为其爱不若燕后。”太后曰:“诺,恣君之所使之。”
于是,为长安君约车百乘,质于齐,齐兵乃出。
子义闻之,曰:“人主之子也,骨肉之亲也,犹不能恃无功之尊,无劳之奉,而守金玉之重也,而况人臣乎?”
【参考译文】
赵太后刚执政,秦国乘机进攻赵国。赵国向齐国求救。齐王说:“一定得用长安君来做人质,才能出兵。”赵太后不答应,大臣们极力劝谏。太后明确地对大臣们说:“有谁再说要让长安君去做人质的,我老太婆一定要吐他一脸唾沫!”
左师触龙请求进见太后。太后怒气冲冲地等着他。触龙慢慢地向前小跑,到了太后面前请罪说:“老臣的脚有毛病,不能快走,所以很久没来看望您了。虽然我私下里原谅自己,可是又担心太后的贵体有什么不适,所以来看望您。”太后说:“我老太婆全靠坐辇走路了。”触龙问:“您每天的饭量没有减少吧?”太后说:“靠喝点稀粥罢了。”触龙说:“老臣近来特别不想吃东西,自己勉强散步,每天走三四里,稍微想多吃点了,对身体有好处。”太后说:“我可做不到。”太后的怒色稍微缓和了些。
左师公说:“我的儿子舒祺,年龄最小,没有出息;可是我又老了,内心很疼爱他,想让他当黑衣卫士,来保卫王宫。我冒着死罪禀告太后。”太后说:“好吧。年纪多大了?”触龙说:“十五岁了。虽说年纪还小,但总想趁着我还没入土就把他托付给您。”太后就说:“男人也疼爱小儿子吗?”触龙说:“比女人还厉害。”太后笑着说:“女人疼爱得更厉害啊。”触龙回答说:“我私下认为您疼爱燕后就超过了长安君。”太后说:“您错啦!远远比不上疼爱长安君!”左师公说:“父母如果疼爱子女,就得为他们作长远的打算。您送燕后出嫁的时候,拉着她的手不让她走,为她落泪,惦念和伤心她嫁得远,也真够悲伤的了。她出嫁以后,您也并不是不想她。每逢祭祀的时候,必定为她祷告说:‘可别让她回来啊!’这难道不是为她作长远打算,希望她的子孙一代接一代地做国君吗?”太后说:“是啊。”
触龙又说:“从现在算起,上推到三代以前甚至到赵国成立的时候,赵王的子孙封了侯的,他们的后代现在还有保住爵位的吗?”赵太后说:“没有。”触龙说:“不仅仅是赵国,各国君主的子孙当初被封侯的,他们的子孙有保持住的吗?”赵太后说“我没听说过。”左师公说:“这就是说他们之中近则自身便遭了祸,远则祸患便落到他们子孙身上了。难道君主的子孙就一定不好吗?不是。是因为他们地位高而没有功勋,俸禄丰厚而没有业绩,但拥有贵重的东西却很多。现在您把长安君的地位提得很高,封给他肥沃的土地,赐给他大量的珍宝,却不让他现在为国立功。一旦您百年之后,长安君凭什么在赵国安身呢?我认为您对长安君打算得太不长远了,所以说您疼爱他比不上疼爱燕后。”太后说:“好吧,任凭你调派他吧。”
于是就替长安君准备了一百辆车子,到齐国去做人质。齐国这才派出援军。
子义听说了这件事,说:“君主的儿子是其亲生骨肉,尚且不能对国家没有功劳而居高位、享受没有功绩的俸禄、拥有大富大贵,何况是做臣子的呢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