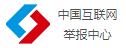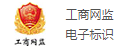桃花鼓声安塞
刘成章
安塞在延安正北,离延安只有四十公里,可是过去由于交通不便,我家的亲戚朋友,去过安塞的屈指可数。只是听说,安塞有个真武洞,那洞很神秘,藏着无数故事,一说可以通到山西,一说可以通到靖边。春天的安塞,满山桃花,老辈人说,每年三月从洞那头吹进去的桃花瓣,直到六月才能从这边飘出来。这个浪漫的故事,使我很是着迷。我班上有个同学是安塞人,他告诉我,从延安西川流来的那条河,就源自安塞。所以那时候,一个满怀好奇心的少年,常常望着滚滚而来的西川河水,充满遐想。
二十多年后的一天,我终于有机会乘车去安塞。安塞路不好走,因为西川河弯弯曲曲,常常挡在路上,大小石头在波浪中出没,这可忙坏了司机的双手,时而换高挡时而换低挡,一个同行者喊道:“哎呀,快把人摇得散了黄了!”
一进入安塞地界,到处是五谷的气息:玉米的、谷子的、糜子的、小麻的、黄豆的、豌豆的,还有地椒的气息、羊的气息。地椒是这里和志丹、吴起一带独有的一种香味浓郁的野草,到处都是。安塞的羊肉味道鲜美,缘于这里的羊吃地椒,仿佛长肉时,便已撒上了香料。
安塞街道不长,宁静安谧,铺面好多都住着人家。这里只有一个供销社和一座国营食堂,要不是挂着一块县政府的牌子,人们也许想不到它是个县城。此时的我,已经工作多年,少年时代的浪漫情怀所剩无几,看见真武洞洞口时,觉得它无非是个较大的山洞。
这是我对安塞最初的印象。
其时我在延安歌舞团从事创作。有一天在院子里,我看见一些农村后生给舞蹈演员示范打腰鼓,那动作如霹似雳,直击人心,顷刻把我镇住了。一问,那些后生全是安塞来的。他们打腰鼓的英姿,出神入化,震荡心魄,那是任何演员都学不来的。这,给我的印象太深了。我自愧虽然去过安塞,却不曾发现安塞还有这样一种灿烂的艺术。
我心旌摇曳,产生了创作冲动,想写一写安塞腰鼓。为此,我又专程去安塞看打腰鼓。安塞这时已修建起相当气派的大礼堂。当时任县文化局副局长的贺玉堂,是一个已经在好几部电影中唱过歌的著名民歌歌手,他在他的办公窑洞,为我放声高歌,那奇高的嗓音,让我叹服。他还就近找了几个腰鼓手给我表演,我再一次被那腰鼓感染了,久久难以平静。然而,几次提笔,又搁下。从生活到艺术,有时不是那么简单,甚至可以说是举步维艰。后来我认识到,那是因为我内心的认知和感情,还未到火候。
又过了好几年,中国迎来改革开放的大潮,人心大顺,万马驰鸣。我去关中西府千阳农村下乡,心里也鼓胀着空前炽烈的激情。结果,只用了两个小时,我就把《安塞腰鼓》写了出来,不久发表在《人民日报》上。就像以前发表作品一样,心里浮起一阵快意,不过很快就烟消云散,一切如常。
后来,这篇文章不断被选入各种散文选本。而且,它好像变成了一群鸟儿,扑棱着翅膀,落上了如大树小树一般的各种语文课本。此时我才意识到,它已成了我的代表作,贴在我的身上了,长在我的身上了。于是,我常常会想起安塞。
去年我回到延安,受邀又一次来到安塞。
汽车沿着宽阔的大路飞驰,一路上桥梁飞架,已没有奔腾的河水挡道。大路平如砥,车如响箭飞。路的两侧,有崛起不久的高楼大厦、石箍窑洞。天上的云,好白好白。偶然也看到了羊群,羊群比云还白。一个老人踽踽前行,折形的镢头朝后挂在肩上,镢把就像一股溪水,沿着他的躯体斜着向下流淌,自在如仙。
蓦然之间,看见了前面的腰鼓山,山上高竖着一个巨大的红色腰鼓,而山下就是安塞市区了。现在的安塞,已是延安的一个区,高楼鳞次栉比,一派现代城市气象。市中心矗着一座金色雕塑,造型是鼓手在捶击腰鼓,充满动感。他的双脚飞舞的场地,是一面大鼓的造型,鼓面光亮,鼓身鲜红。安塞人,已经用腰鼓做了城市的招牌和名片。
而我的注意力,已经落在一些斜背腰鼓的小朋友身上了。那是红军小学的娃娃。他们在语文课上学过我的《安塞腰鼓》,听说我来了,呼啦啦地跑到我的面前,要给我表演打腰鼓。他们的眼神,明亮而炽烈。他们那些好看的小脸蛋上,不知吸收过多少阳光,甜美亮丽。和他们在一起,就像和袅袅上升的地气在一起。他们身上腰鼓的红、背带的红、流苏的红,以及情绪的红,包裹着我,我成了喜庆的中心。
打起腰鼓的孩子们,腿脚欢蹦,精气神四射,鼓槌上的流苏飞舞,用语言极难形容。霎时间,我仿佛看见真武洞里飘出漫天的桃花瓣!人道是“杏花春雨江南”,但这儿不属于江南,而属于北国,是北国里的安塞、粗犷的安塞、强悍的安塞、谷子南瓜苹果飘香的安塞、“走头头骡子三盏盏灯”的安塞,这儿是“桃花鼓声安塞”。在安塞,在日头映红的安塞,在石鲁笔下的火红高崖下,孩子们忘情地歌舞。
杏花的气质是温婉秀丽清清浅浅,桃花的风度是激越轩昂风风火火。如果说杏花的魂灵是水,那么桃花的性情就是火,矢志不渝地燃烧。迎着高原的阳光,那些桃花瓣,从真武洞里飘出极多极多,简直是喷出来的。花瓣一片挨着一片,一片映着一片,上下翻飞;花瓣有如金的质地,铿锵劲舞;花瓣片片散发着香气,展示着这片土地的芳华。而那些孩子们,则是一片环宇的光芒,一群火的精灵。
安塞的丘陵沟壑里,奔腾着不少河流:延河、杏子河、西川河、小川河、小沟河、双阳河……现在发现,在它的地层下,有更多的石油河。整个安塞大地,是包着一团火的。世世代代的安塞人,也像这片土地一样,心底回荡奔突着滚烫的热血。
早在古代,安塞就有“上郡咽喉”之称,常有重兵把守,山山岭岭都回荡过战鼓助阵的声音。唐朝的“安史之乱”期间,伟大的诗人杜甫,望着安塞的芦子关,写下了感时忧国的诗篇。在解放战争中,安塞出过一支英勇善战的游击队——塞西支队,它的队长安塞人田启元更是威名远扬。1947年,西北野战军三战三捷,正是在真武洞,彭德怀将军召开了五万军民参加的祝捷大会,留下了一帧英姿勃发的照片。有人说,冲着安塞一眼望不到头的高山大峁一声喊,随时都会出现九路烟尘、八百悍将、三千五百雷霆。这片土地孕育出的腰鼓艺术,哪能不高迈劲健、威震八方?
眼前是桃花鼓声安塞,是打腰鼓的安塞。这腰鼓的磅礴气势,来自唐宋元明,来自长河落日,来自“天苍苍,野茫茫”,来自中华古老的优秀传统,也寄托着我们新的希冀。想起老人们说的,娃娃们若成了优秀的腰鼓手,一辈子都会蓬勃向上,永不沉沦。
(有删改)
山 峁
刘成章
咔嚓嚓一声巨响,随着神斧的倏忽敛去,开天劈地扬起的亿万吨沙尘,被云推着,被风卷着,被历史堆积着,终于,在苍茫的东方地平线上,赫赫然崛起一片大气磅礴的黄土高原。望天,那么高,那么蓝;望地,那么厚重,那么遒劲;望白杨,那么壮实,那么挺拔。
这茫茫大块上,这雄豪杨柳边,一日,走来一支人数不多的队伍,他们与壮阔的背景相比,微乎其微,犹如一行蠕动的蚂蚁。
他们要去一个预定的地点,可是迷路了。而身后,百倍千倍于他们的敌军,正紧紧追来。
大伙儿焦灼万分。
那边山梁上,一个头扎羊肚子手巾的后生,急匆匆走过。兵荒马乱的,昨夜,他家准备箍窑的钱财被盗了,有人看见小偷现在还藏在山那边的一个庄子,他要赶去捉拿。凭着他的机智和勇猛,十拿九稳,小偷跑不了,石窑还可箍起来。
但那支队伍在拢着手向他大声呼唤。
山听见了,水听见了,他听见了。当他听清是自己的队伍有急事的时候,便踅转身子跑下来了。
这后生,精血蓬勃,一身英气。看见他臂膀上隆起的肌肉疙瘩,就让人感到这高原的坚不可摧;看见他眼中的憨厚而强悍的波光,就让人想起安塞腰鼓何以会挥发出那么奇伟的能量。他毅然放弃了抓住小偷的机会,他毅然慷慨带路,使这支队伍终于转危为安,胜利地到达了目的地。
队伍中的首长,一位个头很高、操着南方口音的人,为了表达真心实意的感激之情,想送给后生一点什么纪念品。可是遍摸周身,别无长物,只摸出一支土产的纸烟,遂以此馈赠。
后生舍不得抽这支烟。当他后来弄清馈赠者是谁的时候,更舍不得抽了。 虽然为了弥补被劫的损失,为了箍起两眼石窑,他土里刨,山上砍,连续苦干了几年,甚至年纪轻轻的就把背都累驼了,但他觉得:值。他觉得他也算为东方世界的天翻地覆,尽到了一点微薄的力量。
好多好多年之后,笔者得知这一动人的故事,翻山越岭,前去造访当年的后生。
不幸得很,他已过早地溘然长逝。他的乡邻中有人叹息着说:他本来可以去北京兜一圈的(只要他把那支烟往手里一举,说当年危难时曾给毛泽东带路并使其脱险,中南海的门卫敢挡?),毛泽东见了一定会把他当上宾待的(还愁没他几个钱儿花?一摞一摞的票子!),可惜他太实受了,没去。他命里没那福分。
人们说,他一直想箍两眼石窑,可是到了儿也没箍起来。人们说,儿孙们把他扶上山之后,烧香纸的时候,把那支烟也一齐向他烧了。这是他生前叮嘱过的。
由当时的生产队长陪同,我攀上一架很高的山,默默地拜谒了他的坟墓。坟墓上荒草萋萋。忽然间,我听见远远的山底下,传来了激越的安塞腰鼓的响声。这使我神思飞荡。我想,他是在一场本世纪的隆隆作响的造山运动中,变成一丘傲然而又朴拙的山峁了。陕北有许多许多这样的山峁。千万丘这样的山峁构成的黄土高原,更加大气磅礴。
(有删改)
转九曲
刘成章
踩着薄薄的积雪,我来到赵家沟了。这儿离延安城八十多里。
我是专为观看转九曲而来的
相传,九曲,又叫九曲黄河阵,是我国古代作战的一种阵法。后来,陕北民间欢度春节的时候,照此阵法布置华灯,让人们在九曲灯火中转悠徜徉,纵情欢乐,这就叫转九曲。
听人说,上院窑里正做灯呢,我于是急切切走去。老远就听见妇女们的说笑声。进窑一看,大姑娘小媳妇的,人人都在忙活:有的做灯盏,有的做灯筏,有的做灯罩。
我实在惊服妇女们的巧手,她们做出来的每一件几乎都是工艺品,都可以拿出去展览。我不由夸赞了几句。一个姑娘却开口了:“老麻子开花转圈圈红,再不要能格滟滟笑话人!”她顺口说出的,竟是十分生动的信天游。我不能不留意她了:穿件红袄,瓜子脸粉白粉白,眉里眼里都像藏着聪明。妇女群中的,还有一个 “巧媳妇”,虽然她已抱上孙子、脸上爬满皱纹了。她正为大灯笼赶做剪纸。我简直目瞪口呆了。她不画任何图样,一剪子下去就剪出一支秧歌队,足有四五十个秧歌队队员,面容迥异,栩栩如生,舞步儿好像还带着风声呢。
晚饭之后,飘雪了。小小的、薄薄的雪花。晚饭的油糕香、馍馍香、米酒香,和雪花的韵味融在一起,在山村蔓延。一整天没有停息的说笑声,也融在里面,更加响亮起来。接着,锣鼓响了,唢呐响了,白狗或黑狗也争争抢抢地叫开了。男男女女,老老少少,秧歌队队员,流水般向学校操场涌去——转九曲的时刻到了!
我夹在人流中,跟着队长大步行走。九曲灯火闪耀在我们眼前了。搭眼看去,繁星点点,光华四射,照亮了山沟,照亮了漫天飞舞的雪花。这灯火,竖成列,横成行,再加上这带着光晕的千万片雪花,造成一片迷迷离离的景致,引人入醉。
锣鼓唢呐声中,秧歌队以“伞头”为前导,首先穿游进灯火之中。“伞头”手中的花伞,应和着锣鼓点,一起一伏,团团旋转,宛若漂浮在九曲黄河的漩涡上;秧歌队队员手中的彩绸,不断地舞起来,像给九曲黄河的上空,抹上片片云霞。花伞旋转时,亮晶晶的雪花也旋转;彩绸飞起时,亮晶晶的雪花也飞起。这花伞,这彩绸,还有这片片雪花、张张笑脸,都被灯火照耀着,都在九曲波涛中旋转狂欢。
秧歌队优美、奔放的舞姿,看得我眼花缭乱,惊羡不已。我跟着群众的队伍,也穿游进去。好像世界上的一切光亮,一下子全聚在这里了。灯是亮的,眼睛是亮的,笑脸是亮的,身影是亮的,连刮的风也是亮的。一片片飘飞的雪花,携着光圈,就像一盏盏飘飞的小灯。我看见,我们这亮亮的行列中,有亮亮的老头,有亮亮的老婆,还有被亮亮的妈妈牵着手的亮亮的孩子。一个个亮亮的,喜眉笑眼,脚步儿轻轻,踩着鼓点,踩着雪花,踩着光亮,欢乐地游转。
我的心头,也亮起来了,升起一道联想的彩虹。我想这一盏盏华灯,多像一朵朵盛开的山花;人们多像蝴蝶飞来绕去,扇动着亮亮的翅膀;我想这一盏盏华灯,多像一穗穗成熟的高粱,人们多像拿着磨了又磨、闪光发亮的镰刀,正在唱出嚓嚓嚓的亮亮的歌声;我还想,这华灯整整齐齐,一行一行,多像一曲美丽乐章的五线谱,多像一根根颤动的琴弦,人们多像飘飞荡漾的亮亮的音符……
一阵哄笑声响起,只见人们一齐向我的身后望去。我忙转过脸,原来是紧挨我的杨大伯,也居然扭起了秧歌。他身上抖下片片光亮、片片雪花。看样子,他曾经定是扭秧歌的好手,胳膊腿儿都透着美感,只是现在为了招人乐,故意把动作搞得非常夸张。待他尽兴之后,我问:“大伯,你多大年纪了?”
“十六了。”他笑答,眉毛上抖下一缕光亮,几粒雪花。
“六十了。”队长解释道,“他小的时候,周恩来同志还教他识字呢。”
“你真幸福呀!”锣鼓声中,我望着大伯,提高了声音。我觉得,我的眼里飘进了一缕光亮,嘴里飘进几粒雪花。
雪大了,纷纷扬扬。雪花上的光晕也大了,一圈一圈。 人们的头上、眉上、肩上,全落上一层雪,又重上一层光,如玉雕一般。雪大情也涨,谁愿离去?人们在光和雪中,更加欢乐地游转狂欢。
过一盏灯,又一盏灯。九曲灯火,好像我们前进的道路。我们的来路是曲折的,去路也是曲折的。但在曲折的路上,在有艰难和痛苦的地方,也像今晚一样,虽然落着雪,总有光辉照耀我们。
(有删改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