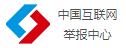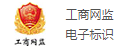静 夜
闻一多
这灯光,这灯光漂白了的四壁;
这贤良的桌椅,朋友似的亲密;
这古书的纸香一阵阵的袭来;
要好的茶杯贞女一般的洁白;
受哺的小儿唼呷在母亲怀里,
鼾声报道我大儿康健的消息……
这神秘的静夜,这浑圆的和平,
我喉咙里颤动着感谢的歌声。
但是歌声马上又变成了诅咒,
静夜!我不能,不能受你的贿赂。
谁希罕你这墙内尺方的和平!
我的世界还有更辽阔的边境。
这四墙既隔不断战争的喧嚣,
你有什么方法禁止我的心跳?
最好是让这口里塞满了沙泥,
如其他只会唱着个人的休戚!
最好是让这头颅给田鼠掘洞,
让这一团血肉也去喂着尸虫;
如果只是为了一杯酒,一本诗,
静夜里钟摆摇来的一片闲适,
就听不见了你们四邻的呻吟,
看不见寡妇孤儿抖颤的身影,
战壕里的痉挛,疯人咬着病榻,
和各种惨剧在生活的磨子下。
幸福!我如今不能受你的私贿,
我的世界不在这尺方的墙内。
听!又是一阵炮声,死神在咆哮。
静夜!你如何能禁止我的心跳?
臧克家与闻一多的师友之谊
臧克家与闻一多既有亲密的师生交谊,又是文艺道路上的诤友知己,两人的交往堪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。
1930年夏天,臧克家就读于青岛大学英文系,由于此时他十分热衷中国文学,故提出转读国文系的请求。当时要求转系的学生太多,恐难如愿,臧克家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拜见闻一多。闻一多时任国文系主任,当他问明臧克家的姓名后,即爽快地说:“你转过来吧,你写的《杂感》我看到了,写得很好!”原来臧克家的《杂感》里有“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,但谁把幻光看作幻光,谁就沉入了无底的苦海”的语句,闻一多特别欣赏。
此后,臧克家便时常出入闻一多先生的办公室,向他请教学问,聆听教诲。闻一多的诗集《死水》出版问世,臧克家倾心阅读,然后挟着自己创作的诗稿向他求教,茅塞顿开,于是断然将自己过去写的诗付之一炬,在闻一多的指导下,重新进入诗的意境。出于对闻一多的崇拜与钦敬,臧克家叩响了闻一多的宅铃,登门拜访。此时闻一多正在研究唐诗,写了一本《杜甫交游录》,臧克家是第一个读者。
谈起诗歌创作,闻一多很赞赏臧克家的才情。当他看到臧克家在《炭鬼》一诗里把挖炭夫的眼睛比作“像两个月亮在天空闪烁”时,便兴奋地从书架上抽出一本诗集,指着说:“你看美国诗人把炭夫额上的电灯比作太阳呢,艺术构思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!”通过闻一多的积极推荐,臧克家的诗作在《新月》上发表了,从此一发而不可收。暑假里,臧克家返回诸城,时有诗情涌上心头,于是奋笔疾书,将稿子寄给闻一多,闻一多收到后认真批阅,其中《神女》一首,在惊句上画了双红圈,臧克家见后高兴得跳了起来。
1932年暑假,闻一多调清华大学任教去了。到了北平,闻一多给臧克家来信说:“人生得一知己,可以无憾,在青岛得到你一个人已经够了。”
1937年6月1日,臧克家特意北上,到清华园看望闻一多。见他住一个小庭院,四面草色青青,一片生趣,依旧那样简陋的书桌,那样的四壁图书。久别重逢,师生相见,分外亲切。闻一多谈他沉浸于《诗经》《楚辞》的研究,臧克家则向先生汇报新诗的创作情状……不料几天后,震惊中外的“七七事变”爆发了。
纷乱中,7月19日,臧克家与闻一多在北平车站相遇,同车南下。闻一多行李简约,臧克家遂问:“先生那些书籍呢?”闻一多情绪沮丧地说:“此行我只带了一点重要稿件。至于图书嘛,如今国土大片大片地丟失,书籍更难顾及了……”闻一多的感慨,使臧克家热泪盈眶。他们在流亡的人群中,好不容易挤上火车,又至天津换车,车至德州站,臧克家下车,辞别闻一多——想不到此次竟成永诀!
这之后,抗日战争如火如荼地展开,臧克家肩负战地宣传任务,到处东奔西跑,但他时时怀念着闻一多先生,当他从报纸上获悉闻一多徒步辗转经湖南去昆明,进入西南联大的消息时,欣喜异常;复闻知先生在联大礼堂神情激昂地朗诵田间的抗战诗,更为喜悦,他禁不住向朋友报捷:“闻先生终于跳出了故纸堆,回到诗国里来了,回到抗日的战场上来了!”他除了不断致函问候外,还将自己的新著寄给闻一多,这就是臧克家1942年在重庆出版的《我的诗生活》一书。投书寄简,杳无音讯,愈加重了臧克家对闻一多的思念。于是,在一天夜晚,他敬师怀友的情感似潮水涌来,便借着一支蜡烛的微光,给闻一多写了一封激情洋溢的长信。果然,闻一多很快回信了。这即是闻一多先生写于1943年11月25日灯下的那封书信。此信首先对臧克家进行了挚意的批评,指出《我的诗生活》只强调了闻一多诗的表现技巧问题,而没从《死水》中看出他的“火"来。信末,他说他正在着手编纂《现代诗选》(《中国历代诗选》的一部分),他让臧克家把自己的诗作寄给他,以供编用。这封长信下笔激情难抑,颇带愠气,随后则如一阵暴雨过后,风和日丽,与挚友侃侃而谈了。
抗战胜利后,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,置中国人民和平民主的愿望于不顾,中华民族重又面临分裂和灾难的深渊。面对此情此景,闻一多,作为一位血性诗人,一名正直的学者,一员民主斗士,他殚精竭虑,奔走呼号,为建立一个光明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,誓与反动派不共戴天。如是,国民党反动派于1946年7月15日唆使特务对闻一多暗下毒手,将这位民主战士枪杀。
闻一多惨遭杀害的消息传出时,臧克家正在南京。7月16日,他行走在南京大街上,见墙上贴有当日报纸,凑过去看,突然觉得脑浆迸裂,头脑懵了,几乎跌倒。他踉踉跄跄回到家里,伏案恸哭。爱人怔怔,臧克家鸣咽着报告噩耗。于是,臧克家与夫人郑曼抱头痛哭,悲伤至极。之后,臧克家含泪写下了《我的先生闻一多》一文,表达了对这位师友的无限追思与悼念。
闻一多的真性情
方子
在世人心目中,闻一多的形象基本上被定格为两种:一是爱国诗人,一是民主斗士。然而很少人想到,闻一多其实是非常有趣的人,他的真性情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魏晋名士。
闻一多在青岛大学国文系任教时,有个叫臧克家的学生前来报考。当年的国文考试有两道试题,其中之一是《杂感》。臧克家的《杂感》只有一首诗,三句话,闻一多却对这三句话无比欣赏,认为它饱含哲理,判了98分。虽然臧克家的数学考了零分,但因为有了接近满分的国文成绩,他才顺利进入了青岛大学,后来成为一名诗人。
中国人历来看重等级,闻一多却更在乎性情相投。臧克家进校后,闻一多非常关心其学业,在写作上更是用心指导。臧克家很快在文坛脱颖而出,发表了大量优秀作品,1933年出版的《烙印》则一时洛阳纸贵。臧克家曾感激地说过:“没有闻一多先生,就没有我的今天。”然而,闻一多并没有将臧克家看作自己的学生,而是视作好友。后来离开青大赴清华执教时,他写信给臧克家说:“古人说,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无憾,我在青大交了你这样一个朋友,也就很满意了。”
真性情的闻一多爱幽默。他教《楚辞》时,常常身着黑色长袍,昂首阔步进入教室,从容地掏出烟盒,问在座的学生:“哪位吸?”学生不接话,他就自己叼上一支,然后边敲桌子边和着节拍唱道:“痛饮酒,熟读《离骚》,方为真名士。”这才开始讲《楚辞》。
快乐时要幽默,无奈时也要幽默。九一八事变爆发,东北沦陷,平津学生纷纷罢课,赴南京请愿,强烈要求国民政府铁心抗日。受此影响,青大学生也在当年10月成立反日救国会,计划南下请愿。校方同情学生的爱国之举,但反对学生南下,闻一多也持这种态度。学生去南京后,闻一多在校务会上主张开除带头的学生,同在青大执教的好友梁实秋也表示赞成。虽然,学校最后只是给这些学生“记过”处分,但学生们对闻一多和梁实秋怀恨在心。
此举使闻一多、梁实秋顿时成为全校学生的“公敌”。学生们贴出“驱逐不学无术的闻一多”“闻一多是准法西斯蒂”的标语。还有人在黑板上画了一只乌龟和一只兔子,标题是“闻一多与梁实秋”。闻一多毫不责怪,反而指着黑板上的乌龟和兔子问梁实秋:“哪一只是我?”“任你选择!”梁实秋故意满脸严肃地回答,说完两人击掌大笑。
闻一多虽然在青岛大学时因为坚持原则而遭到学生反对,但就其一生而言,大家还是非常喜欢他的。否则,他当年家境艰难时,联大同仁不会代他拟刻石润笔启事;他蒙难之后,不会有那么多学生写怀念文章。大家对闻一多的好感,显然与他为人处世的真性情有关。
闻一多兼具才情、真诚与趣味,因此,才让人觉得可敬可爱。